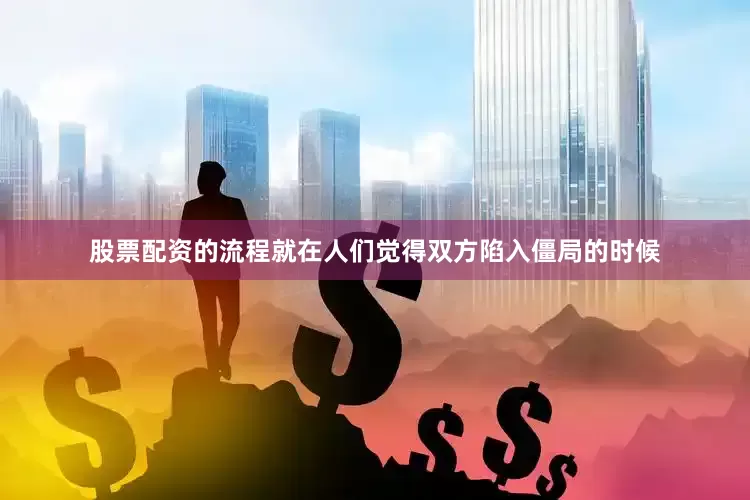“怕死鬼,打什么仗?在这里休息一下,老子去打敌军。”
二团团长钟发生憋着一肚子火,对着旅长皮定均吼出了这句话。战士们已经连续急行军三天,很多人边走边打瞌睡,一头栽进田里是常事。部队抵达安徽凤阳县,刚扒上几口饭,皮定均就下达了立刻出发的命令。
政委徐子荣也觉得不妥,劝道:“休息几个小时,才更有体力走。”但皮定均斩钉截铁地拒绝了:“敌人就在屁股后面,停几个小时,我们就可能全军覆没。这是生死关头,必须走!”
钟发生是皮定均的老战友,此刻也顾不上情面了。然而,面对这句近乎羞辱的咒骂,皮定均没有动怒,只是冷静而坚定地重申命令。这一幕,恰恰是整个中原突围中最残酷、也最考验人性的一个缩影。皮定均真的是怕死吗?恰恰相反,这道看似不近人情的命令背后,是一场早已注定的九死一生的豪赌。

时间回到1946年6月,中原解放区上空战云密布。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万大军,将李先念麾下的六万部队死死围困在鄂豫皖交界的一片狭小区域内,并计划于7月1日发起总攻。为了保存主力,中原军区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:主力向西突围,而皮定均率领的第一旅,则作为诱饵。
皮定均和政委徐子荣接到的是一封特急电报,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当面下达了任务:一旅七千人,必须拖住数十万敌军三天,掩护主力安全渡过平汉线。任务交代完,王树声送他们到门口,压低声音补了一句:“你们几个领导,都准备一套便装。”
这句话的分量,皮定均心里清楚。这是准备让他们在部队被打散后,有机会化装逃生。这既是关心,也是一种不祥的预示。一路上,两人沉默不语。快到旅部时,皮定均突然开口:“我们不准备便衣。”徐子荣的回答同样干脆:“好!我们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。”
他们知道,自己接下的是一个“丢卒保帅”的弃子任务。从一开始,一旅的命运就已经悬在了刀刃上。

往东!向着枪口突围
掩护任务开始后,一旅在前沿阵地加固工事,摆出死守的架势,成功迷惑了敌人。同时,部队白天向东佯动,主力则悄悄向西移动,将敌军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自己身上。三天后,中原主力成功脱险,但皮定均和他的七千弟兄,却彻底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。
接下来往哪走?这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向西追赶主力?等于把敌人引过去。向西北回豫西老根据地?方向太近,风险同样巨大。向南是长江天险,几千人无法渡过。
所有看似安全的生路都被堵死了。经过激烈的讨论,皮定均做出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:向东!东面是敌军重兵集结的区域,还有大别山里盘踞的地方反动武装。这无异于一头扎进老虎嘴里。但皮定均的考量是,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最容易被忽视,而大别山复杂的地形,正适合部队隐藏和打游击。

为了迷惑敌人,政委徐子荣提议,先虚张声势地全线出击,做出要和敌人决一死战的假象,吸引敌人追击,然后迅速脱离接触,折向东方。皮定均当即拍板:“就这么干!关键两点:快和保密。”
连跑带打,人不是铁打的
突围之路,与其说是行军,不如说是一场长达二十四天的逃亡。6月26日,正当一旅与追兵缠斗不下时,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皮定均抓住天赐良机,命令部队全线反击,将敌人打懵后,趁着大雨的掩护,迅速撤出阵地,消失在茫茫雨幕中。
他们躲在刘家村的密林里,不生火,马嘴被捆住,冒着大雨潜藏了一天两夜。随后,部队一头扎进了大别山。一路上,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线,他们专挑县与县之间的交界地带穿行。

在抵达淮河支流淠河西岸的磨子潭时,皮定均预感有埋伏。他急中生智,伪装成当地伪乡长,给霍山县府打了个电话,谎称共军已到磨子潭,询问国军部署。对方信以为真,告知他四十八军的部队半夜就能赶到。挂掉电话,皮定均立刻命令部队抢渡淠河,在敌人包围圈形成前,成功跳了出去。
然而,冲出大别山,进入皖中平原,危险并未解除。身后几个师的敌军仍在穷追不舍。部队只能以每天一百几十里的速度疯狂前进。连续三天下来,战士们的体力被压榨到了极限,这才有了开头在凤阳县的那一幕。
钟发生骂完,皮定均依旧平静,只是催促部队准备出发。钟发生虽然一肚子气,但军令如山,骂归骂,行动上没有丝毫含糊。两个人就像没发生过争吵一样,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行军中。
事实证明了皮定均的判断。正是因为他这份“不近人情”的坚持,一旅才得以在几个小时后,甩开了紧随而至的追兵,并在张八岭的石门山铁路附近,打了突围路上的最后一仗,彻底突出重围。

当他们最终与华中军区淮南大队的同志会师时,这些铁打的汉子们再也绷不住了,抱着战友泪流满面,只有一句话:“我们到家了!”
七千人出发,经过二十四天,大小二十三次战斗,最终五千人建制完整地到达解放区。这在解放战争史上,堪称奇迹。“皮旅”的名号也由此叫响。那个被老战友当面痛骂“怕死鬼”的皮定均,用近乎冷酷的理智,扛下了所有压力和不解,最终带着绝大多数弟兄走出了死亡陷阱。有时候,真正的勇敢,不是不怕死,而是在生死关头,有勇气做出最正确却也最痛苦的决定。
倍享策略-股票配资集中网站-最新配资官网-股票配资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